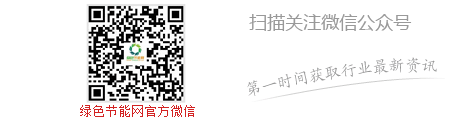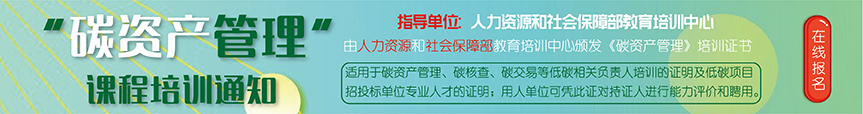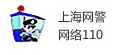上海社會(huì)科學(xué)院經(jīng)濟(jì)研究所副所長(zhǎng)沈開(kāi)艷研究員長(zhǎng)期研究中國(guó)經(jīng)濟(jì)問(wèn)題。2002-2003年間在印度尼赫魯大學(xué)的一段訪學(xué)經(jīng)歷,促使“中印比較”成為她研究脈絡(luò)上的重要一支。她如何看待印度制造的前景和潛力?記者與她進(jìn)行了對(duì)話。
中印比較的立足點(diǎn)該往哪兒放
解放周一:近來(lái),“印度制造會(huì)超過(guò)中國(guó)制造嗎”幾成熱議。您怎么看待這個(gè)問(wèn)題?
沈開(kāi)艷:這個(gè)問(wèn)題值得關(guān)注,要辯證地去看待和討論。
最近這波熱議,讓我聯(lián)想到我從事中印經(jīng)濟(jì)比較研究的緣起,也開(kāi)始思考:這些年來(lái)世界已然發(fā)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,中印兩國(guó)的發(fā)展也越來(lái)越受世界矚目;回顧過(guò)去,展望未來(lái),我們又該把這些比較和關(guān)注,放到怎樣一個(gè)新的坐標(biāo)系中去看待和評(píng)估。
2002-2003年,我去印度做研究,當(dāng)時(shí)的研究專(zhuān)題并非中印經(jīng)濟(jì)比較。直到我完成在尼赫魯大學(xué)的研究回到國(guó)內(nèi),很多國(guó)內(nèi)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者不斷地問(wèn)我,你覺(jué)得印度經(jīng)濟(jì)會(huì)趕上中國(guó)嗎、印度會(huì)發(fā)展得比中國(guó)好嗎?與此同時(shí),一些印度學(xué)者也來(lái)找我交流中印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問(wèn)題。他們關(guān)心的話題,要么是你們中國(guó)現(xiàn)在為什么發(fā)展得這么快、這么好?要么是,你覺(jué)得我們印度能趕上和超過(guò)中國(guó)嗎?這一切,迫使我開(kāi)始深入研究中國(guó)和印度在經(jīng)濟(jì)上的不同表現(xiàn)。
現(xiàn)在想來(lái),那時(shí)的語(yǔ)境背后還有著一種復(fù)雜的情緒。兩個(gè)國(guó)家的學(xué)者雖然紛紛開(kāi)始好奇對(duì)方,但一方面,確實(shí)是互相了解不深,另一方面,心里對(duì)彼此的進(jìn)展也沒(méi)有底,很多道聽(tīng)途說(shuō)的成見(jiàn)占了主流。
但今天的設(shè)問(wèn),顯然已跟十幾年前有所不同。問(wèn)題非常明確,就是直接問(wèn):印度制造會(huì)超過(guò)中國(guó)制造嗎?
解放周一:您從設(shè)問(wèn)的立足點(diǎn)看到了不同?
沈開(kāi)艷:是的。這是一個(gè)比較大的變化。
比如原來(lái)問(wèn)的是,印度經(jīng)濟(jì)會(huì)超過(guò)中國(guó)嗎?這種“超過(guò)”其實(shí)可以通過(guò)任何方式,比如增長(zhǎng)速度、貿(mào)易規(guī)模、產(chǎn)業(yè)結(jié)構(gòu)等。但現(xiàn)在就是集中問(wèn)制造業(yè)。
這樣一來(lái),這個(gè)設(shè)問(wèn)里就暗含著兩個(gè)前提。第一,有些問(wèn)題不必再問(wèn),比如印度的信息產(chǎn)業(yè)會(huì)超過(guò)中國(guó)嗎?印度的生物制藥會(huì)超過(guò)中國(guó)嗎?因?yàn)榇鸢缸悦鳌5诙@個(gè)提問(wèn)暗含著這樣一個(gè)潛臺(tái)詞:即便中國(guó)的制造業(yè)非常強(qiáng)大,但印度已經(jīng)可以作為一個(gè)可能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對(duì)手來(lái)做比較了。
任何提問(wèn)都不可能是空穴來(lái)風(fēng),一定是有了一些苗頭,才會(huì)被提出來(lái)。比如《今日印度》最近披露的一組數(shù)據(jù)說(shuō),近幾年,印度制造業(yè)增長(zhǎng)率已經(jīng)從原先的每年1.7%左右,增長(zhǎng)到了如今的每年12.6%左右。這個(gè)增長(zhǎng)幅度相當(dāng)明顯,很難不被關(guān)注。
只討論誰(shuí)超過(guò)誰(shuí)太簡(jiǎn)單
解放周一:印度制造會(huì)否超過(guò)中國(guó)制造,目前學(xué)界對(duì)這個(gè)問(wèn)題怎么看?
沈開(kāi)艷:現(xiàn)在對(duì)這個(gè)問(wèn)題有兩種看法。一種觀點(diǎn)認(rèn)為,印度制造在短期內(nèi)不可能超過(guò)中國(guó)。主要理由是,印度經(jīng)濟(jì)總量目前只有中國(guó)的五分之一,人均GDP僅為3000美元左右(而中國(guó)是將近8000美元),且印度有非常多的遏止制造業(yè)發(fā)展的因素。比如落后的基礎(chǔ)設(shè)施、糟糕的營(yíng)商環(huán)境、數(shù)億文盲、嚴(yán)苛的勞工法等等。這種觀點(diǎn)占大多數(shù)。
但有些學(xué)者從另一個(gè)角度去看,認(rèn)為這是可能的。理由是,印度的市場(chǎng)規(guī)模很大,有大量成長(zhǎng)中的中產(chǎn)階層,這將為其制造業(yè)發(fā)展提供廣大的市場(chǎng)和消費(fèi)需求;印度人有熟練運(yùn)用英語(yǔ)的語(yǔ)言?xún)?yōu)勢(shì),技術(shù)人才儲(chǔ)備充裕,對(duì)歐美專(zhuān)利體系熟稔;特別重要的一點(diǎn)是,印度有制造業(yè)最需要的青年勞動(dòng)力。
解放周一:但您似乎對(duì)上述這些目前已經(jīng)比較主流的觀點(diǎn)并不盡然贊同。您是怎么看的?
沈開(kāi)艷:我們不妨回看一下這兩個(gè)國(guó)家各自的改革開(kāi)放歷程。
上世紀(jì)80年代初,中國(guó)改革開(kāi)放政策剛出臺(tái)時(shí),適逢全球范圍內(nèi)的制造業(yè)轉(zhuǎn)移浪潮一浪高過(guò)一浪。世界主要發(fā)達(dá)經(jīng)濟(jì)體由于受到本國(guó)勞動(dòng)力成本上升、商務(wù)成本上升、環(huán)境資源約束等限制,制造業(yè)發(fā)展出現(xiàn)了比較嚴(yán)重的危機(jī),必須尋求向發(fā)展中國(guó)家的轉(zhuǎn)移。而彼時(shí),占世界人口最大比重、占世界土地面積很大比重的中國(guó)正式宣布對(duì)外開(kāi)放,無(wú)疑為這些尋求投資去向的制造業(yè)資本提供了一個(gè)絕佳場(chǎng)所。
那時(shí)的中國(guó),不僅擁有著充沛的勞動(dòng)力供給、勞動(dòng)力成本極低、國(guó)內(nèi)市場(chǎng)容量急速擴(kuò)大、商務(wù)成本極低等優(yōu)勢(shì),且尚未在生態(tài)、資源和環(huán)境等方面過(guò)分苛求,因此也敞開(kāi)雙臂歡迎外國(guó)資本和技術(shù)的進(jìn)入。正是由于這些外資的推動(dòng),中國(guó)制造業(yè)的出口得以迅速擴(kuò)大。全球制造業(yè)向中國(guó)轉(zhuǎn)移,成為一個(gè)不可逆轉(zhuǎn)的潮流和趨勢(shì)。
印度是到1991年才真正對(duì)外開(kāi)放的。此時(shí)新一輪的信息科技革命浪潮已開(kāi)始席卷全球。印度現(xiàn)代服務(wù)業(yè)的增長(zhǎng)有兩個(gè)最重要的原因:一是新技術(shù)的應(yīng)用和自由化改革,提高了行業(yè)本身的勞動(dòng)生產(chǎn)率。二是國(guó)外市場(chǎng)需求——即外包服務(wù)市場(chǎng)的不斷擴(kuò)大,為行業(yè)發(fā)展提供了新的空間。為此,印度更為重視的是服務(wù)業(yè)。印度的服務(wù)業(yè)發(fā)展首先得益于因特網(wǎng)經(jīng)濟(jì)的迅速發(fā)展,這使得服務(wù)業(yè)的外包與分工可以分散到全球各處。
而與此同時(shí),印度恰好擁有人力資源數(shù)量?jī)?yōu)勢(shì)和較好的高等教育資源條件。印度目前有約12億人口,且人口年齡結(jié)構(gòu)很年輕,這是印度最重要的勞動(dòng)力資源。印度的高等教育也很發(fā)達(dá),在培養(yǎng)學(xué)生的創(chuàng)新精神和與國(guó)際接軌等方面,明顯領(lǐng)先于中國(guó)高校。印度精英教育更是為印度培養(yǎng)了一大批通曉英語(yǔ)的國(guó)際化管理和科技人才。
綜上可知,所謂“一方水土養(yǎng)一方人”。光比較這兩個(gè)國(guó)家具體走什么道路,并無(wú)太大意義,更多要看他們是否在時(shí)代機(jī)遇面前,迅速找到了機(jī)遇同自身比較優(yōu)勢(shì)的結(jié)合點(diǎn)。以此類(lèi)推,未來(lái),中印兩個(gè)國(guó)家,在制造業(yè)的發(fā)展上,也將走出立足于本國(guó)基礎(chǔ)且適合自身國(guó)情的道路。從這個(gè)意義上講,只是討論誰(shuí)超過(guò)誰(shuí),太失之于簡(jiǎn)單,也沒(méi)有什么意義了。
印度制造的優(yōu)勢(shì)和潛力
解放周一:雖然按照普遍的分析,印度制造短期內(nèi)對(duì)中國(guó)制造并不構(gòu)成挑戰(zhàn),但它有沒(méi)有哪些優(yōu)勢(shì)和潛力是中國(guó)所沒(méi)有的,恰好又是我們以后應(yīng)該重視的?
沈開(kāi)艷:先說(shuō)說(shuō)當(dāng)下印度發(fā)展制造業(yè)方面的優(yōu)勢(shì)吧。
第一,印度現(xiàn)在的勞動(dòng)力成本非常低。這個(gè)跟我國(guó)已經(jīng)形成一個(gè)鮮明的對(duì)比了。且印度不僅人口充裕,近十年來(lái),印度制造業(yè)的勞動(dòng)報(bào)酬增長(zhǎng)非常緩慢,至今每小時(shí)不到1美元。
第二,印度制造業(yè)從產(chǎn)品設(shè)計(jì)理念到銷(xiāo)售渠道的思維方式,都非常接近歐美高端市場(chǎng)。相較而言,我們的思維方式就更固板一些。
第三,印度雖然在一般制造業(yè)上根本無(wú)法同我國(guó)匹敵,但在生物醫(yī)藥、電子通訊、航空航天等高端精工領(lǐng)域有非常好的積累和表現(xiàn)。
第四,印度在自主創(chuàng)新能力上更強(qiáng)一些。從基礎(chǔ)教育到高等教育,印度在課堂教學(xué)中都很注重對(duì)創(chuàng)新能力的培養(yǎng),科研機(jī)制有很多自己的優(yōu)點(diǎn),有鼓勵(lì)創(chuàng)新、寬容失敗的社會(huì)氛圍。
第五,在服務(wù)外包領(lǐng)域經(jīng)驗(yàn)豐富,擁有大批國(guó)際化的信息技術(shù)人才。為什么蘋(píng)果、華為等一些手機(jī)硬件制造商要到印度去,因?yàn)樗麄兛粗辛擞《仍谙嚓P(guān)衍生產(chǎn)業(yè)上的配套能力和服務(wù)優(yōu)勢(shì)。
第六,印度在知識(shí)產(chǎn)權(quán)保護(hù)的某些方面相對(duì)來(lái)說(shuō)比較到位,比起中國(guó)要好一點(diǎn)。
相較而言,中國(guó)的劣勢(shì)可能不僅反映在勞動(dòng)力成本、土地價(jià)格、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已容不得半點(diǎn)破壞、本土資本熱愛(ài)追逐經(jīng)濟(jì)泡沫等方面,中國(guó)制造現(xiàn)在碰到的最大瓶頸,是管理的方式方法;碰到的最大外部問(wèn)題,是來(lái)自美歐等發(fā)達(dá)國(guó)家的貿(mào)易保護(hù)主義和貿(mào)易壁壘。
解放周一:可見(jiàn)印度制造的后發(fā)力還是很強(qiáng)大的。不知道未來(lái)整個(gè)世界制造業(yè)的版圖會(huì)否由此發(fā)生一些變化?
沈開(kāi)艷:中印兩國(guó)的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到目前的階段,接下去的進(jìn)一步發(fā)展都面臨著各自的瓶頸與制約。中國(guó)的發(fā)展瓶頸問(wèn)題包括不健全、不規(guī)范的金融體制以及市場(chǎng)潛規(guī)則,政府能否處理好與市場(chǎng)之間的關(guān)系、不對(duì)經(jīng)濟(jì)活動(dòng)過(guò)多干預(yù),人口老齡化及社會(huì)保障,環(huán)境保護(hù)、污染治理和節(jié)能減排等。印度的發(fā)展瓶頸包括長(zhǎng)期存在的宗教矛盾與種姓制度,嚴(yán)重落后的基礎(chǔ)設(shè)施建設(shè)和城市發(fā)展,脆弱的工業(yè)體系,特別是制造業(yè)的不發(fā)達(dá),數(shù)量巨大的文盲和貧困人口,等等。
這些瓶頸主要是制度層面和社會(huì)層面的問(wèn)題。在今后的發(fā)展中,中國(guó)和印度誰(shuí)先突破了這些瓶頸,誰(shuí)就能贏得進(jìn)一步的發(fā)展空間和增長(zhǎng)潛力,其經(jīng)濟(jì)社會(huì)的發(fā)展速度和質(zhì)量,也會(huì)明顯提高。
話又說(shuō)回來(lái)。哪怕印度制造上去了,會(huì)對(duì)中國(guó)構(gòu)成一些壓力,但也可能是機(jī)遇呢?如果印度可以成為一個(gè)更開(kāi)放的市場(chǎng),或者擁有更好的基礎(chǔ)條件,你也可以去投資,你的潛在市場(chǎng)會(huì)更大,整個(gè)亞洲市場(chǎng)可能都會(huì)被進(jìn)一步帶動(dòng)起來(lái)。
中印間的互相了解還遠(yuǎn)遠(yuǎn)不夠
解放周一:事實(shí)上,印度制造謀求新氣象,也給了中國(guó)制造一個(gè)認(rèn)識(shí)自己的對(duì)比樣本。在您看來(lái),我們國(guó)內(nèi)的中印比較研究,接下來(lái)需要更多關(guān)注哪些議題,才能跟上時(shí)代的變化?
沈開(kāi)艷:總體來(lái)說(shuō),國(guó)內(nèi)完全專(zhuān)注于印度經(jīng)濟(jì)研究的學(xué)者還較少。國(guó)內(nèi)學(xué)者對(duì)印度的研究,更多集中在國(guó)際問(wèn)題、外交關(guān)系、文學(xué)藝術(shù)、宗教文化等領(lǐng)域。
這會(huì)產(chǎn)生什么問(wèn)題呢?就是當(dāng)我們需要真正做出一些客觀的比較時(shí),難免會(huì)帶著一些局限性和固有的偏見(jiàn),很多印度人研究中國(guó)問(wèn)題時(shí)也會(huì)這樣。從長(zhǎng)遠(yuǎn)來(lái)看,這不利于兩國(guó)之間形成一種冷靜、客觀的思考與對(duì)視。
近年來(lái)對(duì)中印經(jīng)濟(jì)的關(guān)注提示我,有一些問(wèn)題是必須要回答了。比如,從發(fā)展質(zhì)量來(lái)看,中印兩國(guó)都曾是經(jīng)濟(jì)水平貧窮低下國(guó)家,正在經(jīng)受著因經(jīng)濟(jì)高速增長(zhǎng)所帶來(lái)的雙重利弊考驗(yàn)。國(guó)家富裕了,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;工業(yè)化發(fā)展了,但相應(yīng)的城市化發(fā)展滯后了;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了,但資源環(huán)境壓力增大了; 經(jīng)濟(jì)現(xiàn)代化指標(biāo)提高了,但是人文社會(huì)發(fā)展被忽視了……下一步,怎么補(bǔ)“短板”?
又如,從產(chǎn)業(yè)結(jié)構(gòu)來(lái)看,中國(guó)走了一條傳統(tǒng)工業(yè)化發(fā)展的道路,以制造業(yè)為核心,帶動(dòng)其他產(chǎn)業(yè)的發(fā)展,最終帶動(dòng)整個(gè)國(guó)民經(jīng)濟(jì)的發(fā)展;印度則依靠軟件業(yè)等信息產(chǎn)業(yè)和現(xiàn)代服務(wù)業(yè)的發(fā)展,繞過(guò)工業(yè)化階段而直接進(jìn)入后工業(yè)化階段,成為“世界辦公室”。目前看來(lái),印度似乎在產(chǎn)業(yè)結(jié)構(gòu)上更接近西方國(guó)家,但回過(guò)頭來(lái)看,印度是否需要補(bǔ)制造業(yè)發(fā)展的課?印度的“跳躍模式”可持續(xù)嗎?若能持續(xù)關(guān)注印度產(chǎn)業(yè)政策的演進(jìn)和重點(diǎn)產(chǎn)業(yè)的發(fā)展脈絡(luò),相信也將對(duì)中國(guó)具有非常大的啟示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