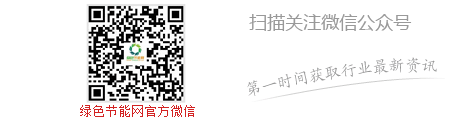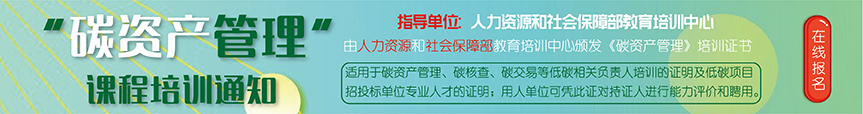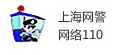一張是灰色的空白圖,圖片說明的大意是:這拍的是故宮,多美啊,你看到了嗎?
另一張圖,由14張小圖構(gòu)成,14個畫面都是從同一個角度俯瞰北京CBD核心區(qū),連續(xù)14天不間斷拍攝出來的。
兩張圖的轉(zhuǎn)發(fā)量不分伯仲。但圖片背后的人,彰顯的反思態(tài)度卻大不同。前一張圖是作圖軟件制成的,嚴格地說,那不是照片,而只是一個創(chuàng)意。后一張圖是一個普通網(wǎng)民,14天里不間斷地端著同一架相機,站在同一個位置,以同樣的參數(shù),按下快門。
前一張圖解構(gòu)、嘲笑了這場霧霾。后一張圖,一個普通人以最樸實的鏡頭語言,記錄了北京最近14天的天氣。
一假,一真。一戲謔,一嚴肅。一感性,一理性。而后者正是這場霧霾話題討論中,最稀缺、最不易陷入“霧里看花”的姿態(tài)。
其實,大家都明白污染不全是政府的事兒,很多人都有私車,有諸多不低碳的行為。從某種意義上說,霧霾里,人人都是顆粒污染物的制造者。一場霧霾,人人有責。
但在網(wǎng)上,有時只剩下一種聲音:一味地罵,扔完“磚頭”就閃人,圖一時痛快說不負責任的意氣之辭,把網(wǎng)絡(luò)當泄憤的意見菜市場。甚至出現(xiàn)了“大霧里出門遛狗,牽回來的是別家的狗”等各種狗血劇一樣的段子。
正如那張憑空創(chuàng)作的沒有故宮的空圖一樣,點擊量很高,笑聲很大,可笑完了,又怎樣?霧霾散了嗎?
說到底,抱怨、戲弄是低效、無用的。 與其那樣,不如去做些什么。面對霧霾,每個人都難以逃避。政府做政府該做的,公民做公民該做的。
政府必須負起責任來,眼下最容易做也最應該做的是驅(qū)散“信息上的大霧”,消除各種信息的不對等,給公眾知曉權(quán)。政府在第一時間公布數(shù)據(jù),發(fā)布權(quán)威解釋,記者不用四處堵專家,聽眾多專家說意見打架的“我覺得……”,真相就不會“像霧像雨又像風”。
其實,這場霧霾里,就算環(huán)保部門不公布任何數(shù)據(jù),氣象臺不發(fā)布黃色預警,每個人的身體也都是監(jiān)測器、預警器,人人都能感知到“老天變臉了”。
“監(jiān)測數(shù)據(jù)和群眾感受不能‘兩張皮’,必須把人民群眾對環(huán)境的切身感受與監(jiān)測數(shù)據(jù)統(tǒng)一起來”,不能“人民群眾深受污染之害、苦不堪言,而監(jiān)測數(shù)據(jù)喜氣洋洋、自說自話”。環(huán)保部部長周生賢不久前的這兩句話,在這場霧霾里,真可謂切景切題。
再反觀我們自己,每個人都與這場霧霾脫不了干系。上下聯(lián)動的環(huán)境問題中,公眾不應該是冷嘲者和圍觀者。環(huán)境問題絕不僅僅跟國家產(chǎn)業(yè)結(jié)構(gòu)調(diào)整、節(jié)能減排這些“大”有關(guān),也與我們每個人的“小”相關(guān)。
我們出行不離汽車、過度使用空調(diào)、愛使用一次性筷子、工作浪費紙張、點菜不注意分量、洗澡愛用盆浴等等,這些點滴小“罪”,都最后轉(zhuǎn)化成空氣里的污染物。
當我們調(diào)侃著這場霧霾是適合“草船借箭的日子”,在家關(guān)緊門窗,坐在空氣凈化器旁,采取所謂“自救”時,不妨稍稍反思下我們自己。或者,干脆從起身關(guān)掉電腦開始。
沒錯,“從我做起,從現(xiàn)在做起”,幾乎是環(huán)保話題長年不衰的終結(jié)詞,從哥本哈根會議,到貴州最偏僻鄉(xiāng)村的環(huán)保課堂,概不例外。可正是這老生常談的9個字,是解決諸多環(huán)保問題的真武器。
霧霾終會散去,可這個終結(jié)詞永不會散去。
讓我們再回頭看那個用14天記錄北京天氣的攝影者,我們不知道他的職業(yè)、身份,這個眼睛藏在取景框后面的人,只是選擇了自己認為對環(huán)保有用的方式,在網(wǎng)上表達他個體的“民意”。也許,和你我一樣,他不懂什么專業(yè)的環(huán)境數(shù)據(jù),也分不清霧和霾的區(qū)別,但他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——端起相機。看來,很多網(wǎng)友讀懂了他,回帖中,很多網(wǎng)友在反思政府的同時,沒忘記反思自己。
這個網(wǎng)民的小舉動,無異于穿破重重霧霾的一縷陽光。(從玉華)